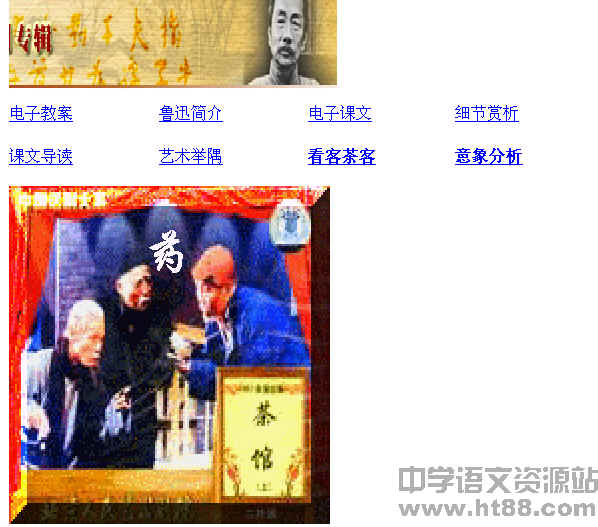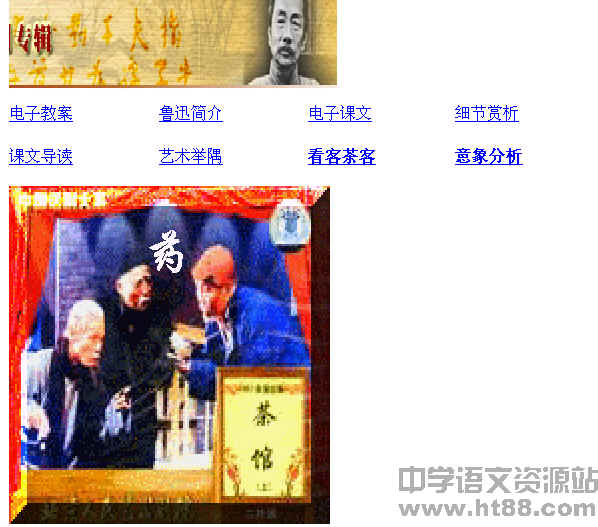
谈《药》的花环
在《药》的第四部分,写了夏瑜坟上“分明有一圈红白的坟顶。”对于这个花环,一般教学参考书及其他分析材料,都大致理解为如下两点:第一,夏瑜的死并非全无意义,还有人在纪念他;第二,给人以“热度”和“亮点”,以免太消极了。按照这种理解,我们发现这个小小的花环与整个小说至少有两处不协调的地方。
其一,这个花环与小说的批判性主题不协调,或说花环与主题存在冲突。
鲁迅在小说中以冷峻的笔调,叙写了一个触目惊心的吃人血的故事。仁人志士在为国为民流血牺牲,而华老栓(群众的代表)却在买志士的血、吃志士的血,这是一个怎样悲哀而残酷的故事!写它的目的,就在于“揭出病苦”,表现批判性主题。写得愈残酷,其揭露批判性就愈深刻。其实鲁迅先生在小说中有意强调突出了这种残酷性。排开“吃血”这个典型的“残酷”不论,我们还发现其他几处被强调的“残酷”。小说第三部分写茶店“谈药”一段。这一段有不少人物登常如康大叔、红眼睛阿义、驼背五少爷及花白胡子的人,他们不懂得夏瑜的事业和夏瑜的死,那还算不得残酷,那是由于他们的职业和身份所限。而“‘阿呀,那还了得’坐在后排的一个二十多岁的人,很现出气愤模样”。曾是进化论者的鲁迅先生,竟写出了一个二十多岁的人的“气愤”来,这份残酷意味,想必不难体会。我们再看第四部分夏四奶奶给儿子上坟一段。夏四奶奶“有些踌躇,惨白的脸上,现出些羞愧的颜色”!知子莫若母,连母亲也认为儿子死得不光彩,这是怎样一种令人心寒至极的悲哀和残酷啊!从中我们也不难体味鲁迅强调这种残酷性的深意。即:强调了这种残酷性,也就强调了小说判批性的深度;消弱了这种残酷性,也就削弱了批判性,而这小小的花环,恰恰冲淡了从小说一开始直至结尾都被强调了的残酷性,因而也就冲淡了小说主题的浓度。
其实,我们知道写这个花环,并不是鲁迅先生的原意,也并不是他的原始构思。鲁迅在《呐喊·自序》中解释说,是“听了将令”,“平空添上一个花环”,“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”。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从“听了将令”,“平空添上”中,看出这个花环与整个小说的不协调意味来呢?
其二,这个小小的花环与小说第四节的整个坟场环境、气氛不协调。
寒冷的清明时节,坟场丛冢累叠。冷风、枯草、秃枝、乌鸦,一派萧条冷落,荒凉寂静的景象。甚至阴森森的,令人毛骨竦然。不难看出,鲁迅在这一节是有意突出这种“鬼气”,以强调夏瑜死后的悲凉。但是这个小小的花环却冲破了这种“鬼气”,这种悲凉,而与整个坟场环境氛围发生冲突。
可以肯定地说,坟场的“鬼气”,夏瑜死后的悲凉,是鲁迅要表达的本意,与原始构思的主题是一致的。也正是这种“鬼气”,这种悲凉,才能使小说主题得以表现并深化。从某种意义上讲,这种“鬼气”悲凉的程度,正是小说主题深度的量度。也只有这种“悲凉”的结局,才能和小说前部分所展示的主题相一致、相贯通。
那么,没有了这花环,是不是就会显出些“消极”意味来,这恐怕是一个不能轻易断定的问题。笔者以为这个小花环,在“五·四”前夕那种社会现实情况下,确能给人以鼓舞等。但是,同时也应指出,作为经典文学作品,这个花环与原始构思及小说主题是有冲突的。
因此,在教学中,当讲这个花环时,笔者窃以为应把握一个“度”。如果过分渲染这个花环的积极作用,大讲其“光明”,过分强调其“亮点”、“热点”,都将会使学生对这篇名作的主题理解产生一定的难度。